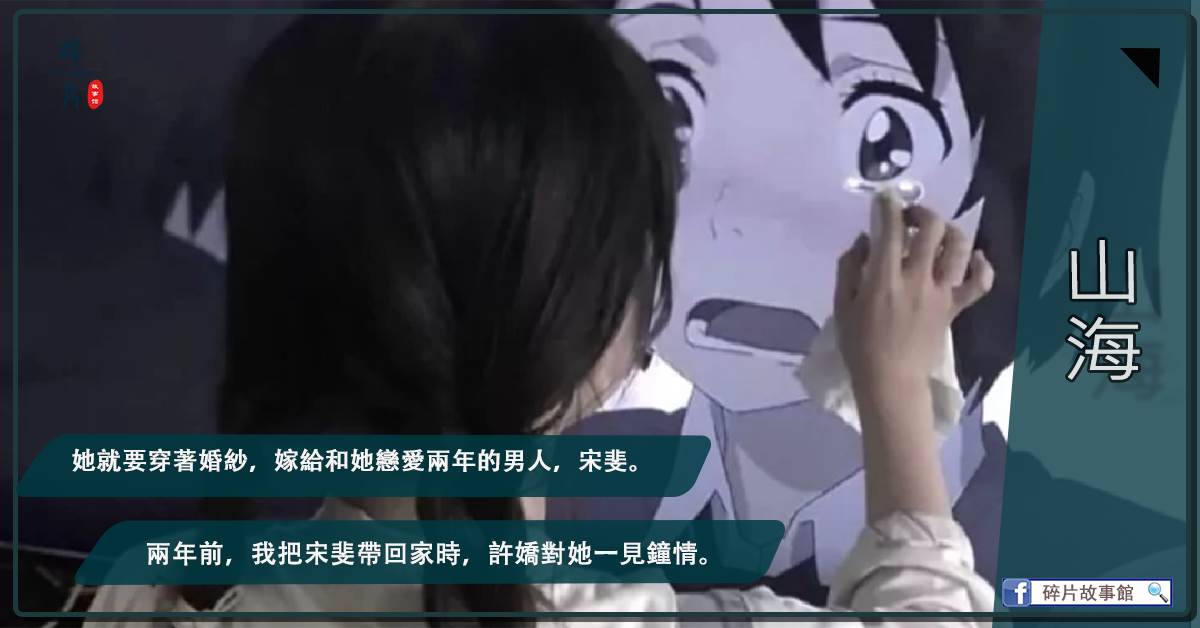《山海》第3章
而,跟爸媽許澤后。
許澤著,爸媽后座。
空蕩蕩副駕,直以都留許嬌。
面,著們言語議論罪過。
「就麼,個,連姐姐婚禮都愿回參加。」
媽疲倦靠爸肩膀,「得自己教育真很失敗。」
爸疼拍拍:「養熟狼,值得為費神。」
扭過,仔仔細細觀察們表。
試圖從面到怕絲。
沒。
突然失聯,只讓們得惱憎惡。
ADVERTISEMENT
沒個,秒鐘懷疑過。
,事。
靈魂,竟然還流淚。
邊流淚,邊笑著問:「媽媽,真真,過嗎?」
「麼,為什麼?」
同樣問題,很久之也問過次。
初,習很緊張。
爸談業務,許澤紀還,許嬌剛。
媽得腎結,每醫院兩照顧,累瘦圈。
媽好像也容,個比許澤更零。
遇鄰居,跟夸好幾遍,懂事,孝順。
ADVERTISEMENT
被同欺負,至趟,為。
好像切都往好方面展。
直到午,們起過馬,麼,挽。
樣母女親昵,對實太過陌。
幾乎識,揮,以至于踉蹌著后退兩步。
正值昏。
燈轉。
輛轎呼嘯著從們邊擦過。
媽神又變。
種很熟悉淡。
繃著,淡淡:「果然養熟狼。」
,幾乎被懊悔茫然所措吞沒,拿圓規自己胳膊扎好幾個窟窿。
猜你喜歡
溫馨提示
加入尊享VIP小説,享受全站無廣告閲讀,海量獨家小説免費看
進入VIP站點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