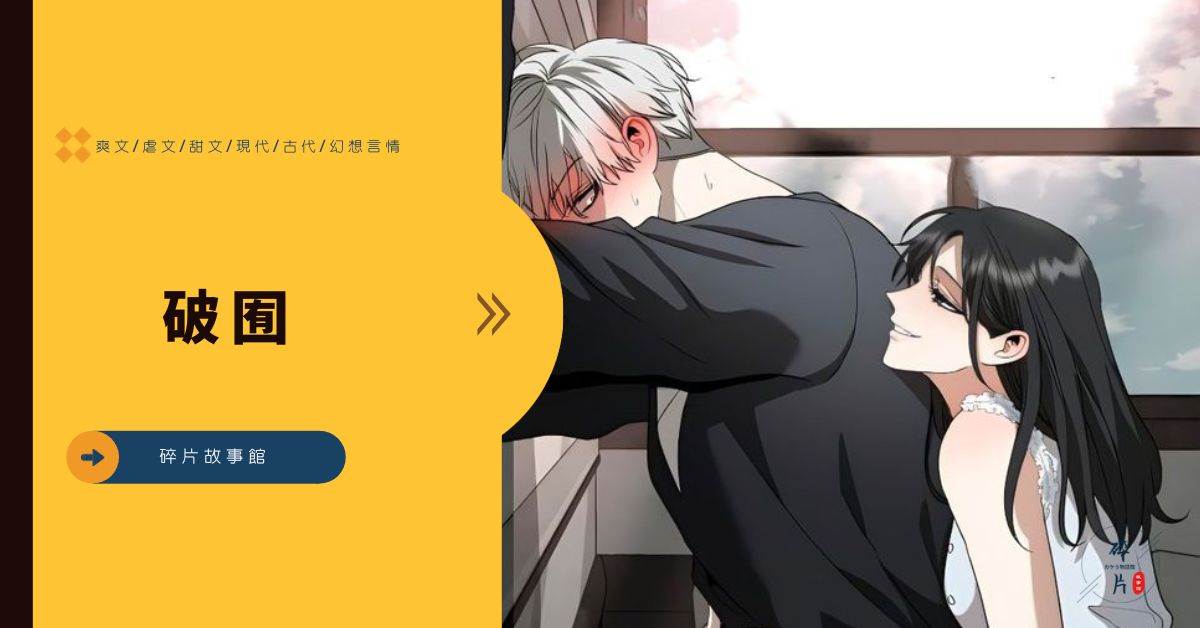《破囿》第3章
」
說完,他就雷厲風行地聯系人幫我聯系人,然后弄到了一個學籍。
只不過,不是攻擊系,而是輔助系。
但這些都無所謂,軍校也沒說不能跨系選課啊。
學籍一辦好,我的光腦就納入了軍校學生的信息,明日就能刷卡進校。
司烈還想說什麼,我已經迫不及待地翻身壓在了他身上,雙手按住他古銅色的健碩胸膛,甚至捏了捏那塊彈性十足的肌肉。
「大人,您這樣幫我,我無以為報,」我做出一副情深不悔的模樣,「但我一定努力,早日讓您擁有自己的孩子。
ADVERTISEMENT
司烈一愣,然后就被我堵住了唇。
一開始,他還有些驚奇與享受。
「我還從沒被女人壓過。」
半小時后,他奪回主動權,滿身大汗,氣喘吁吁。
三次后,他發現事態不太對勁:「等等……」
夜色漸濃,他被迫激活血脈,變出了一定獸形,然后被我提溜著尾巴和耳朵玩來玩去。
第一次遇到這種可以 rua 的小獅子,我一時激動,忘了收斂。
于是一晚上過去,這個為了尊嚴死也不愿意開口說「我不行了」的男人眼下烏青,嘴唇泛白,儼然一副與段玨同病相憐的腎虧模樣。
ADVERTISEMENT
甚至比段玨還慘。
我伸了個懶腰,神清氣爽地去給他喂水喂飯。
他勉強睜開眼,可以說是奄奄一息: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我不勝嬌羞:「大人,怎麼啦?」
司烈:「……」
他半晌才艱難地說完整一句話:「你們嗣族,都這樣?」
我困惑地問:「都哪樣?」
司烈:「……」
他大概是后知后覺,明白了段玨那種樣子的由來,臉色就跟調色盤似的。
猜你喜歡
溫馨提示
加入尊享VIP小説,享受全站無廣告閲讀,海量獨家小説免費看
進入VIP站點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